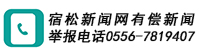老张的好天气
融媒体讯 老张翻了一个身,醒了。透明的窗户告诉他,天该亮了。于是一咕隆爬起身,下了床,走到阳台上,望了望东边的天空,暗蓝暗蓝的,没有一丝云彩。九月的山风迎面拂来,带着一丝凉意。经验告诉他:不错,今天又是个好天气!他想下一趟方山,到镇上去办几件要事,不想赶上坏天气。
他扯下不锈钢管上的抹布擦了擦并没有灰尘的不锈钢围栏。这崭新的楼房住着就是舒服啊,比茅房亮的早。他远眺近看了一番,山庄还在沉睡着。回到床头边,移开枕头,掀起棉絮,一层,两层,摸出一个暗红的塑料袋,小心翼翼地打开,又是一个硬质的塑料袋,方方正正的折叠着,他一层一层地退开,露出一摞存折,五保的,粮补的,养老的,还有一本是弟弟家的,最后一本被套上了一层透明的薄膜,显示出了它的特殊身份,折子里还夹着一摞红钱和几张零币。他拉亮壁灯,打开这个特殊的折子,仔细端详了一会上面的数字,又用指尖沾了点唾沫,数了数红钱,不错,一千元整,数过好多遍,这里有上次中心小学里那个梅校长送给他的两个红包,400元。梅校长是乡里派来扶贫的,每次来总是带些米呀油的,上次来说是空手,就给了他一个红包,还有一个是给弟弟的,谦让了好几回,梅校长硬是塞进了他的衣兜,那就只有恭敬不如从命了。他今天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将这钱和其他折子里面取出的钱一齐存进那个具有特殊身份的折子里,似乎只有这样才放心,而且看着里面的数字不断增大,是一种说不出的舒坦愉悦。他又依次将折子、钱装进薄膜袋里,一层一层地依旧折叠起来,塞进衣兜里,扣上扣子,轻轻地拍了一下,哼着即兴的黄梅小调,下了楼。其实他这次下山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上次梅校长来时对他说过,小侄子在中心小学读书,国家每学期要补助500元钱,8月31日前打进粮补折子里。他常常惦记着这钱到账没有,再者也想看看自己最疼的小侄儿在校生活怎样,这侄儿是他兄弟俩的根系所在,承祧着两房香火,丝毫马虎不得。弟媳一打电话就问小侄儿的情况,现在去看过究竟,正好可以回她。想起弟媳他就恨,一连生了三个女娃儿,四十多时才生这个小侄儿,常年在外东躲西藏,让弟弟耗尽了家底,如今五十多岁了,还得外出打工。他总是焦急这个穷坑如何填得起,幸好祖宗保佑,国家扶贫政策来了,弟弟列为低保,一年生活补助好几千块,而且二侄女读大学,一年可贷款八千,三侄女读高中,一年补助二千,就连小侄儿读小学,每年也补助一千,而且每天中午还有营养餐,白吃白喝。最高兴的是去年,政府补助兄弟俩每人两万,促成了这三间两层的小楼房。想起这些心中不免又得意起来,很快洗漱完毕,锁好门,按了按衣兜,迈开大步上了大路,整个山乡还是沉浸在一片寂静之中。
现在的政策就是好,村子里每一个角落每一条路都硬化了,杨不起半点灰尘。走过农家乐广场的时候,他不由自主地想起狗儿他娘一伙人每晚在广场上蹦来跳去时的神态,如今的女人越来越没规矩啦!音乐搞得震天响,挺着个大屁股,装模作样,在广场上扭来扭去,没有一点农家女人的规矩。他正愤然着,一声笛响吓了他一大跳,几辆小车、摩托悄无声息地从他身边滑过,他本能地朝路边闪了闪,这才发现自己已下到了半山腰。
山脚下,钓鱼台水库笼罩在一层薄纱之中。沿水库一圈满满的都是曾经的记忆。那时候,一条小船,从一个汊里到另一个汊里,从一个码头到另一个码头,一声声的吆喝:“三河啊——”“朱湾啊——”“坝上!坝上!”;一声声的呼唤:“有——船——么——”……划船的大多是女娃,嗓门尖,性子急,经常抢他的号,他无所谓,从不计较。每天驮着两片木浆,早出晚归,一天虽然挣不了几个钱,但很快乐。自从库北、库南路通车后,这一切归于寂静。划船的女娃子都分散漂向了沿海各个城市。他没读过一天书,人又木讷,不敢出门,以至于一直找不到老婆。想到这里似乎恨起这公路来——当年可是有几个女孩子暗示过喜欢他的。
一路想着,到镇上时红日才刚刚爬上山顶,这天气就是好!他见银行还没有开门,决定先到学校里去。轻车熟路找到了梅校长——期初侄儿报名的时候一切都是这校长代办的,他由此很是得意,邻里间述说了好几天,毫不吝啬地将校长演绎成了自家亲戚。梅校长将他引到侄儿宿舍,他摇了摇侄儿的新铁床,觉得挺稳实的,很是满意,替侄儿整理了一下凌乱的被褥,问了几句琐事,然后掏出钱袋,一层层剥开,抽出一张十元地递给侄儿,再三叮嘱不要乱用,依前折好钱袋放进衣兜,扣好扣子,使劲一摁,转身和梅校长告别,又说上一叠客套的话,出了校门,到街边花两元钱买上一杯豆浆两个馒头,边走边吃边喝。
等到老张从银行里办妥一切出来的时候,已是日上三竿了。阳光暖暖地罩在身上,他感觉自己已出汗了,果然是个好天气。(通讯员 邓金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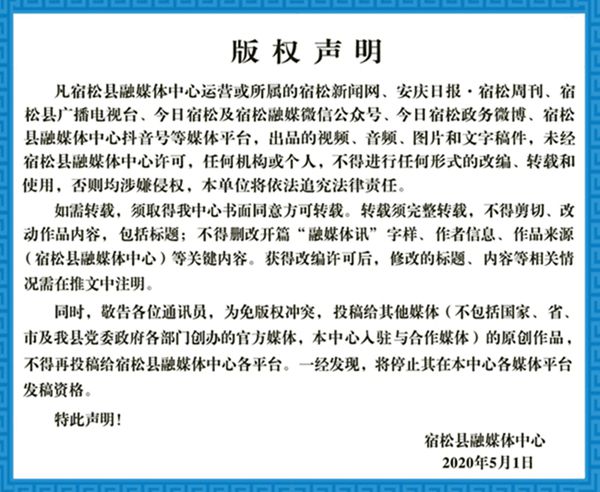
责任编辑:融媒体中心 朱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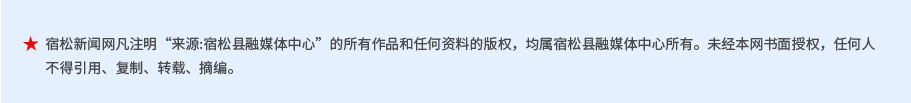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