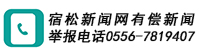那 牛 , 那 狗
那头耕牛,给我童年留下美好的回忆,流着泪、蹒跚着步伐,后面跟着一只“汪汪”叫的黑狗,在全家人默默注视下被买牛人牵走,画面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1979年责任田分到各家各户,“僧多粥少”几家共分一条耕牛。我家和福春爷爷家分到的黄牛力气大、个头高、脚步勤,根据人口算牛在我家养10天、福春爷爷家养8天,如此循环。
放牛是小时候的乐趣。一群放牛娃约好,什么时候到哪座山头集中放牛,玩的开心。我们变着花样玩,有用布蒙着眼睛凭声音来抓人的“摸猫儿”,或抓子、或跳岗、或斗鸡、或捉羊等等,满山是我们的笑声和打闹声。玩着玩着,牛或跑到庄稼田地里,被“看禁”的老头抓住会罚上一碗米,回家免不了享受“竹笋炒肉”的皮肉之苦。
牛为了地盘,也会斗。我家牛个头高、力气大,识相的牛会远远躲开,不服的干,直到服为止,此时我感到自豪,似乎是我干了胜仗。黄牛干仗是“干不过就跑”,不比水牛,红着双眼往死里斗拼个你死我活,对周边人极具威胁。那时大多养的是黄牛,牯牛稍长大时都会阉掉,性格会更温顺,正如此大人才放心这些小屁孩放牛。
大人犁田时,我不能离开随时准备放牛,我也乐此不疲,空隙间可以抓几只肥大的蝗虫,蝗虫的大颚及强壮的后足很有攻击性,冷不丁会把手弄破皮。只要迅速按住它的背部,在挣扎的时候用手抓住翅膀的根部就基本搞定。卸掉它的后足、扯掉它的翅膀丢进水田里任其挣扎,偶尔带回家丢给鸭子或鸡,追逐着分享美食;或抓一只大青蛙,“青蛙是益虫”从不舍得吃,抓了又放、放了又抓。也或舀干水沟,用小手一层一层扒开厚厚的泥巴,泥鳅拼命钻泥不过是徒劳,运气好的话会弄上一碗泥鳅。最期盼的是福春爷爷犁坂田,田泥随着犁头翻转,躲在泥田里的黄鳝无处遁匿,又是一顿佳肴。
我看牛非常用心。“双抢”时牛的工作量大、用的苦,看着被鞭抽的伤痕十分心痛。为让牛吃饱有力气,我趁大人回家吃饭的工夫把牛牵到田埂上,那里草很肥很深很嫩。看着黄牛贪婪地、津津有味的样子非常开心。牛蝇牛虻忘我地叮咬黄牛,我会毫不犹豫一巴掌拍下去从来顾不得脏。如果用小棍轻轻挠在牛的两股之间,它会放慢脚步、翘起尾巴很受用的样子。中午牛拴在树影下休息,惬意昂起头半躺在地上反刍——听得出是嚼草的声音,悠闲的神态十分享受,牛眼半眯对我眼,彼此用心在交流。
我对牛有最愧疚的一次。牛在专心吃草,我拍打牛头上的牛蝇,“呼”的一下黄牛一甩头,腮帮甩到我身上。“靠,连我都敢顶?胆子肥了?”将牛绳系在松树上,收紧绳子让牛鼻子几乎贴着树干动弹不得。“看你顶我,看你顶我!”拿起鞭子狠狠抽它头部,一鞭下去一条痕,牛躲着可无法躲,无助的眼神在委屈流着眼泪。出了“恶气”接着放牛,它又一甩头,原来是身上许多牛蝇在叮它。错怪黄牛了,我摸着我给它留下的伤痕满满的内疚。
我慢慢长大,牛慢慢变老,黄牛“干仗”胜的几率少多了。我寄宿在校读书,只是偶尔放牛。
“牛现在老了,要卖掉。”一次听到爸爸同妈妈商量,那是一个秋风萧瑟的阴天。
爸爸说了也就定了,过了几天一个贩牛的来了,围着黄牛转了转、看了看,评头论足。
万物有灵,何况是同我一家人生活了十年的老黄牛。牛一定听懂了,从此无助的眼神,一直流着眼泪。
“爸爸,不要卖吧,牛整天都在哭。”大姐姐对爸爸说,自己的眼泪也下来了。秋收刚过,都是坂田,为了在牛被卖前将田全部翻过来,姐姐每天牵着老黄牛耕田。耕着田、流着泪,大姐陪着流泪。
“你看,牛老了如果死了我们什么都没有,趁现在还能卖个千把块。”爸爸何尝舍得同我家共同生活十多年的老黄牛?是老黄牛在我家最困难的日子任劳任怨为我家犁田耙地,已经是我家的编外人士。没有办法,真的需要钱。
一个秋日的下午,买牛的过来牵牛。我家养的小黑狗“汪汪”对着牛贩子叫。这只小黑狗惹得我第一次挨了妈妈的揍,我记忆中的唯一一次。记不清那狗从哪里来的反正就到了我家,“来来来!”我跑狗追,快追到我后一个转身,狗往我身上跳。狗的爪子厉害,几次挠破了皮。妈妈拿根棍子打我——她每次都是打到地上,我大声哭着持续了个把小时。“儿,真给打到了么?”妈妈见我哭着不停以为打痛了看看我的伤势,这么一安慰我似乎更委屈哭声更大了。就这黑狗,我放牛时跟着我,拴牛的绳子在地上拖时小狗会在后面追着。那牛、那狗,还有我,一道永恒的风景。
“回来!”黑狗一直追着牵牛人。
全家都是依依不舍。老牛迈着蹒跚的步伐,被人牵着,后面跟着“汪汪”的小黑狗。夕阳西下,走在水库坝上,牛的身影拉得老长老长。“哞——”老牛满是悲壮的叫声似乎诉说这什么,爸爸转过身去,偷偷擦拭眼睛……
那狗从此也不见了。那牛,那狗,是我永远抹不去的记忆。(作者/刘玉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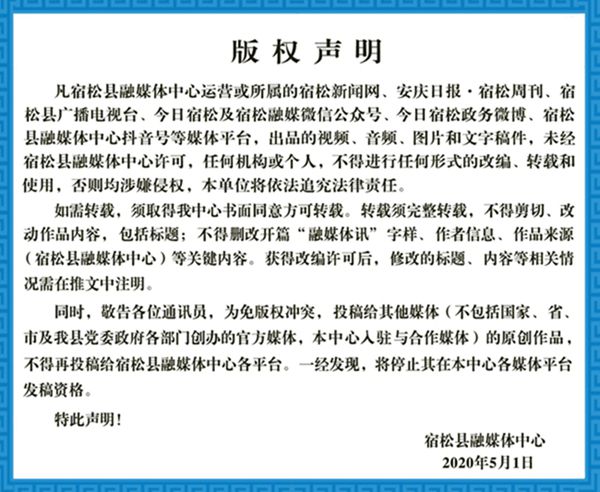
责任编辑:融媒体中心 汪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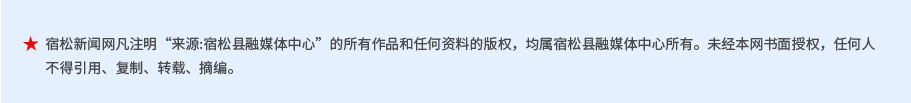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