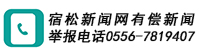父亲
年年清明,今又清明,清明时节倍思亲,我怀念我的父亲。
总想着提笔写一写父亲,但又怕写不好,一直未动笔,这次,在这个清明节,我坐下来,静下心,要为我的父亲写点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故意铺垫和渲染,只有朴实无华的叙述。
我的父亲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辛劳一辈子,苦了一辈子,总不能想,一想到父亲的音容笑貌就有想哭的冲动。父亲生于1962年,2013年不幸罹患脑癌离开了我们,在人世间只待了短短五十一载。
爷爷奶奶共孕育了十个孩子,只有四个长大成人,两男两女,父亲是长子,深得爷爷奶奶宠爱。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整个大家庭把最多的爱护给了父亲,但这些“过分”的爱也造就了父亲懦弱的性格。
父亲未上完初中就辍学了,听爷爷讲,不是家里不让他读,确实是父亲读书成绩跟不上。父亲没读书后就跟着爷爷做生意,那时候家里做油面,做好后挑着担走村串户卖。父亲口讷,做生意不愿大声吆喝,有时候早上挑一担面出去,到傍晚回来还是原样,一点没卖掉。爷爷看父亲不是做生意的料,又安排他跟人家学木匠。学木匠要到师傅家去住,师傅家的一切大小事务都要帮忙,估计师傅脾气不好,喜欢骂人,父亲待了很短的时间,坚持不下去,背着行李回家了。
待在家里总不是事,爷爷又安排父亲跟舅爷爷学石匠,那个年代的石匠不像现在的石匠这样吃香,建房子的人家也少,石匠没啥用武之地。父亲跟着舅爷爷几年,苦吃了不少,却没学到啥东西。那时候很注重兴修水利,父亲跟着舅爷爷天天在河坝上抬石头、砸石头、垒石头,不仅没学会建房子的技术,还因为抬很重的石头留下了腿部静脉曲张的后遗症,父亲的小腿部总是青筋暴起,看着挺吓人的。就这样,学石匠手艺的事情也搁浅了。
转眼父亲20出头了,到了婚配的年纪,在舅奶奶的保媒下,跟我母亲结婚了。母亲跟我讲过,当时她没看上父亲。因为啥呢?因为一件小事,一天,父亲去外公家接母亲,那时都是走路,从外公家到爷爷家要经过一处河堰,在跨过一处小溪流的时候,父亲摔倒在水里,全身都湿了,母亲就此认定父亲“没本事”,回去就不愿意跟父亲。外公年轻时性格暴躁,母亲怕外公。外公家里那时候特别穷,爷爷家条件要好很多,爷爷常指使父亲挑点米,挑点柴到外公家,农忙的时候,丢掉家里的事不做,去帮外公家插秧、割谷。父亲的示好得到了外公的认可,在父母之命大于天的年代,母亲就此跟着父亲一块生活了,先后生下了三个姐姐和我。
家里的孩子多了,家庭开支就多了,干农活挣不了几个钱,迫于生计,九几年的时候,父亲跟着同乡的人到九江建筑工地去打工了,因为没手艺,干的是最累的活——拉板车。这一拉就是七八年,全家的生活开销,我们四姐弟的学费都是父亲一车一车拉建筑材料挣回来的。就连家里盖平房,盖房子用的瓷砖和木窗都是父亲从九江工地上淘回来的。
那时候我还小,每次父亲去九江,我问他去哪?母亲会告诉我说:“爸爸出去挣钱。”“挣钱”,宿松话叫“勤钱”,“勤”就是找的意思。小小的我天真地以为:外面的世界到处藏着钱,只要眼力好,到处找找就能捡到钱,想想真是好笑。每次父亲从九江回来都会带点小礼物给我们姐弟四个。我印象中第一次吃香蕉就是父亲带回来的,家里的黄山牌黑白电视机是父亲扛回家的,当时高兴得不得了,还记得,三个姐姐每人一块梳头镜也是父亲从外地带回来的。
有一年,父亲从九江回来,应该是夏季农忙的时候。一天晚上,父亲去管秧田里的水,因为没有穿胶鞋,被蛇咬了,一只小腿肿得老高。父亲在家修养了一段时间没有出门,被蛇咬了也没有去医院,只是派我和三姐每天清晨去田坝上找一种紫色的小花,回家捣成泥状敷在蛇咬的伤口上,神奇的是最后竟也痊愈了。
98年,家乡发大洪水,那年我七岁,对两件事印象很深,都是有关父亲的。
一件事是父亲带我到河边洗澡。那年夏季水大,水一直涨到了家门口的“下边”(地名)。记得有一天傍晚,村里好多大人带着小孩到水边戏水,父亲也带着我,还帮我带了换洗的衣服,怎么帮我洗的我没印象了,我只记得我怕羞,叫父亲带我到河边的庄稼地里换的衣服。
另外一件事是全家总动员抢收被水淹的稻谷。家里有一块“大田”(我们家给那块田名的名,田块的确大)就靠近河边,田里种的稻谷都成熟了,被大水淹了。为了减少损失,全家人都出动,趟水抢救稻谷,用家里的“火桶”(以前宿松人家里冬天取暖的设备,木头做的,整个人可以坐在里面取暖)在水面来回运。我也跟着家人到了抢收现场,当“火桶”从岸边划到稻田的时候,里面是空的,父亲就把我放在里面,自己在水里走,推着火桶,我就感觉是坐在船里一样,可高兴了。
九十年代末,江浙沿海一带经济发展很快,家乡陆续有好多人去那边打工。1998年秋季的时候,父亲带着辍学的大姐到浙江打工,人生地不熟,吃了很多苦,租的房子离工厂比较远,为了早点到厂里避免迟到被辞退,父亲在那一年学会了骑自行车。
第二年,母亲带着我也到了浙江,跟父亲和大姐团聚,我转到那边的小学读书。而二姐和三姐跟着爷爷奶奶成了留守儿童。
到浙江后,为了省钱,爸爸租了面积很小的一间房,那间房只放了一张上下铺的铁床和一个灶台,就显得很拥挤了。父亲当时在一处沙厂上班,为了方便,也为了给我们腾地方,他搬到沙厂旁边的工棚去住了。在沙厂,父亲做最辛苦的活——上沙子,沙厂没有铲车,有车来拉沙,父亲就跟同事一锹一锹的往车上装。
我只记得有一个夏天的周末,学校放假,母亲带着我,买了两个西瓜去看父亲。到沙厂后,看到父亲颈上搭条毛巾,晒得黢黑,正满头大汗地卖力装沙子,看到我和母亲来了,他朝我们笑,他的那次笑我永远也忘不了。
母亲傍晚的时候回去了,留我在简陋的工棚陪父亲住一晚,我记得第二天早上,父亲还给我买了美味的肉包子当早餐,我猜想,他平时肯定舍不得买。
我在浙江待了一年半,2000年的时候,奶奶因病去世,父亲母亲带着我回家奔丧。第二年,母亲和大姐还到浙江打工,父亲则留在家中种庄稼,照顾爷爷、二姐、三姐和我。这跟村里其它人家不一样,别人家都是妻子留守,丈夫出门打工,而我家是父亲留在老家。
刚开始几年,多是二姐、三姐洗衣服做饭。后来,二姐、三姐相继到初中去了,在校住宿,只有周末才回家,我还在读小学,是父亲每天早上拖个洗衣凳到塘边洗衣服,那些在塘边洗衣服的女人总是笑父亲,父亲倒是一副无所谓的表情,陪着笑,也不去讲什么。但是年少的我当时心里却很不是滋味,开始在心里瞧不起父亲,觉得他太老实,太没用了。
从小学三年级一直到高三都是父亲在家陪着我,母亲和姐姐们在外打工,只有每年过年的时候匆匆回家几天。在这期间,我没有给父亲多少好脸色,倒是父亲倾其所有地爱着我。在老家,他种点庄稼,刚开始几年种得多点,后来种庄稼越来越不划算了,他就种得很少了。到我上高中那几年,他就完全跟着石匠做小工挣钱没有种庄稼了。跟着石匠做小工很辛苦,父亲每次傍晚回来都是满身泥浆,一身臭汗。
父亲对自己很吝啬,对花在我身上的支出就很大方,特别是学习上的。记得上五年级的时候,可以连电视屏幕的那种游戏机特别火,我骗父亲说:“那是学习机,能提高成绩,我同学都在用。”我央求父亲给我买一台。那个机子当时可不便宜,一台机子的价钱相当于父亲做三天小工的工钱。我以为父亲不会买。一天下午放学,我刚回到家,父亲就拿出一台小霸王“学习机”递给我。我高兴坏了,我的是村里同龄孩子中的第一台“小霸王”,当时被小伙伴们羡慕着心里美滋滋的。“小霸王”并没有被我拿来学习,尽打游戏去了。
我上初中时,对父亲印象最深刻的事应该是他自己动手在老屋凭一己之力盖起了一间带猪舍的茅厕,还有一间牛棚。那时候家里种了庄稼,需要用牛。从我记事起,家里就是养了牛的,都是爷爷在看管,我上小学还经常放牛。我还记得是一头大水牛,牛是跟村里另外一家合养的,约定好你家管几天我家管几天,要用牛的时候也协商好。
猪舍盖起来后,父亲买了一头黑猪仔,父亲对那头猪好得不得了。猪舍几乎天天打扫,猪食里掺许多白米饭。天气好的时候,还把猪从猪舍放出来,让猪晒太阳、拱树根、滚泥水。猪身上长虱子了,父亲给猪挠痒让它躺下,帮它除虱子。在父亲的精心“伺候”下,过年的时候,那头猪养到近三百斤。父亲对猪好,可能是纯粹为了多杀肉,因为我养的狗就很不受他待见。
猪舍和牛棚只用了一两年,我们就搬离老屋了,勤劳的父亲母亲操持着在大路边上盖起了楼房。
初中、高中,我都是住校,只有节假日才回家,上初二的时候,爷爷去世了,二姐和三姐也辍学打工去了,母亲和大姐一直在浙江打工,只有过年才回家。平日里,只有父亲一个人在家,这导致了他后来变得越来越寡言少语。
可能是因为实在无聊吧,在我上高三的时候,父亲被人带着迷上了赌博,在人家家里聚众“推牌九”,输赢很大的那种。有一个周末,我从学校回家,父亲不在家,别人就跟我说了,讲父亲最近都没有做事,常往谁谁谁家去,那里是打牌人去的地方。傍晚父亲回家,我问他去哪了,他说做工去了,我看他身上干干净净的,根本就不像干了一天活。那晚我大发雷霆,当着他的面摔了几只塑料桶,晚饭也没吃。我从来没有发过那么大的火,父亲估计也吓到了,像个受了惊的孩子呆坐在椅子上很长时间。打电话跟母亲讲了家里的事,母亲在电话里跟父亲吵了架,并叫我向父亲要存折看,父亲不情愿的把家里的存折交到我手上——一天之内取三次钱,每笔都在千元以上,我知道父亲赌博肯定输了不少钱。我跟母亲商量怎么处理,最后的处理方式是叫父亲把家里的存折送到小姑妈那里,由小姑妈暂管,让父亲没有钱参与赌博断了他的念想。也许是我摔桶的行为触动了父亲,后来他就收手了。
那件事发生后,我就怨父亲。有一次他到学校给我送肉加餐,下午站在学校大门口等我放学出来,我出来的时候远远的看见他了,却下意识的躲着他走。他在放学的学生人群里没有找见我,又把肉送到我在校外跟同学合租的房子(学校宿舍条件太差,没人住),把煮好的骨头肉交给我,叫我在房东那里热一下吃掉。当时不想跟他多说话,满口答应,催促他快回去,他走后,我把肉直接倒掉了,现在想想真是不应该。
那段时间,也正是高三的关键时期,我的成绩却直线下降,那是致命的。2010年,我的第一次高考,我住在学校统一安排的宾馆里,没让父亲送。考试那两天都在下雨,雨还下得不小。虽然我坚持叫父亲不要到县城陪考,但是每考完一门从考场出来,都能在雨中的人群中看到翘首企足等待的父亲。每次出来我跟父亲招呼都没打,就径直跟同学一起回住宿的宾馆吃饭,也没想他当时有没有吃饭,在哪里吃饭。整个考试考完,回家的路上,他问我考得怎么样,我就回了他一句不咋样,我们就沉默了一路。
高考成绩出来了,不出所料,我考得不理想。我不甘心走一个差学校,强烈要求复读一年,父母亲都支持。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商量的,“高四”那年,父亲外出打工了,母亲回家陪我。那一整年我没有跟父亲联系,母亲到县园区的一家服装厂上班,在裁床车间干很辛苦的“拉布”活。我还像以前一样住校,一个月回一次家。
复读那一年,我心无旁骛的学习,2011年第二次高考,取得了还算理想的成绩,进入了大学。
我读大学后,家里没了牵挂,母亲也外出务工了,去到父亲工作的那边,这么多年了,他们终于团聚在一起了。
不幸发生在我读大三上学期的时候,那天中午放学后在食堂吃完饭回寝室,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母亲跟我说,他跟父亲在合肥的医院里,我心里咯噔一下,紧张起来。追问母亲发生了什么事,母亲起初不敢对我说实话,怕我接受不了,只说父亲经常头痛,检查后医生说是有一个良性肿瘤,开刀切除就没事了。我能感受到母亲在电话里说话哆嗦,很不正常,叫母亲有事别瞒我。其实母亲是骗我的,父亲得的根本不是良性肿瘤,而是脑癌中最严重的胶质瘤四级晚期。
当从母亲口中听到“脑癌”两个字的时候,感觉身上有一千斤的重物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眼泪夺眶而出。
在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我向辅导员请了假,从学校赶到合肥省立医院南院,见到憔悴的母亲和躺在病床上输液的父亲,又一次泪奔。
见到父亲,还没等我安慰他,他就笑着先安慰起我来,跟我说:“没事的,不用担心,我头痛是小时候耳道发炎引起的后遗症,以前也发过,不碍事。”家里人都瞒着他,他不知道自己生了多大的病。
在医院输液四五天了,父亲的主治医生还是没有安排父亲做手术,父亲急了,要求出院回家。在医院,每天就床位费和输液的费用一天要一两千,医生再不给手术真的有点耗不起。通过打听知道,要想早一点排上队手术,需要给医生打点。我委托一位亲戚给主治医生塞了2000元红包,过后效果立马有了,医生通知第二天手术。挺恨那位医生的。
手术那天,家里的主要亲人都赶过来了,父亲的手术从上午九点钟一直到下午两三点钟,我们都在外面焦急地等。父亲从手术室里被推出来后,麻醉还没有过,但是意识是清醒的,我紧紧握着他的手,他的眼里噙着泪。
父亲被护士医生一起抬到病床上,大脑缠着纱布、有引留管,身上还有导尿管,手上在输液,为了防止父亲麻醉失效后,因为疼痛乱动弹,护士将父亲的手脚全部绑起来。当天晚上,父亲麻醉失效后,疼痛难忍,我和母亲一晚没睡,就坐在父亲床边陪着他。
因为姐姐们实在脱不开身,我又跟辅导员请了半个月的假,跟母亲在医院照顾父亲。医院有规定,陪护只能一个人,晚上陪护床位也只有一张,白天我和母亲轮流照顾,晚上母亲睡陪护床,因为是夏天,我就到医院外买了泡沫地板,铺在医院的走廊上,就那样将就了七天。七天后,父亲从合肥转到了县人民医院,又住了一个星期,渐渐的恢复了体力,我们就回家了。
回家后,母亲每天精心做各种大补的食物给父亲吃,一个月不到,父亲因为手术变得羸弱的身体恢复到了之前健康的状态,一家人都很高兴。但是我心里知道,父亲的好转只是暂时的,脑癌胶质瘤在大脑中是浸润型生长,手术根本割不干净,就像割韭菜一样,割完还会再长。
父亲好转后,我就回学校上课了,之后妈妈带着父亲还到合肥做过两次化疗,两个人对合肥都不熟,跑了不少冤枉路。
农历七月初三,是父亲的生日,那天母亲特意杀了一只鸡给父亲庆生,父亲也很高兴,但是一碗鸡肉端给父亲,他还没吃到一半,突然身体抽搐,重重的摔倒在地,把我们吓坏了,赶紧拨打了120。等120车赶到时,父亲又缓过神了,跟没事人一样,我知道父亲脑中的定时炸弹开始读秒了。120车上的医生向我了解父亲的病情,我如实说了,在医生建议下,父亲没有再去住院。
到此时,父亲还不知道自己得的是绝症,以为经过一次大手术身体就没事了。但是从生日突发抽搐开始,他的身体和精神就一天比一天查,脾气也越来越大。
因为脑中的肿瘤在生长,他的颅内压越来越高,压迫到神经,视力开始下降,发展到有一只眼睛看不见,到最后双眼都看不见。由于肿瘤的扩散,由刚开始仅仅头痛到最后全身痛,开始吃几粒小小的止痛药还有效果,最后需要我一周去县医院买一次吗啡回来,每天打两针。第一次请的村卫生室的医生帮忙打的针,后面医生就不愿意来了,没办法,不能看着父亲痛,我自己买来注射器,在网上搜打针技巧,自己给父亲打。到父亲临终时,手臂上全是针眼。除了打止痛针,还需要配合冰敷大脑,父亲才会舒服点。整天整夜的疼,整天整夜的喊,后期半个月除了喝点水,没有进一点食物,父亲身体从一百四五十斤变得只剩骨架子,母亲都能轻松的抱起他。我可怜的父亲,在生命的最后,受尽了病痛的折磨。
父亲的生命像油灯一样,渐渐微弱。于2013年农历十月初五早晨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我怀念我的父亲。
——儿子孙良高泣笔
责任编辑:宿松新闻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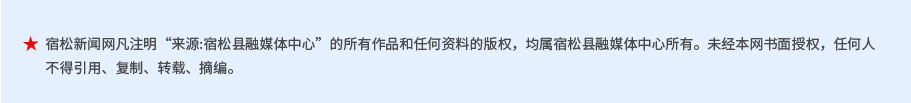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